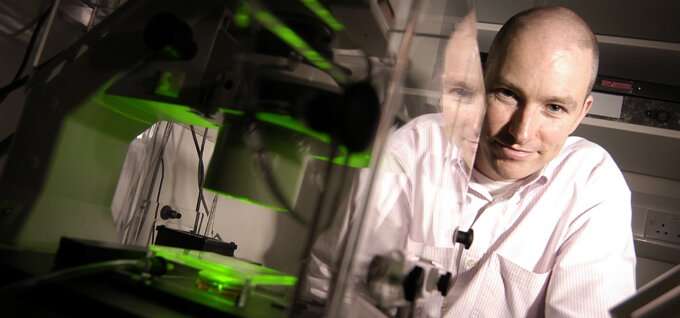教授斯蒂芬·泰勒。来源:英国癌症研究
一个活的生物可以支持先进的卵巢癌的新疗法的发展。我们遵循英国资助癌症研究团队的旅程为卵巢癌构建一个活着的生物。
早在2015年,史蒂芬·泰勒教授有一个计划。15年之后学习细胞分裂在细胞系,他想测试如何anti-mitotic化疗药物干扰这个过程更临床相关的设置。
泰勒和他的团队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癌症分工科学中极力避免与细胞系相关的一些问题。良好的文档记录,他们往往不能反映原始肿瘤和很少有任何相关的临床信息。所以,他们开发了一项计划,检查微管稳定剂紫杉醇引起的精确信息癌症patient-derived原发性卵巢癌细胞死亡细胞。
就项目而言,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我认为,让我们从患者获得细胞,”泰勒回忆说。“让我们建立与医院的合作对细胞活检和测试我们的假设。”
通过实验室的位置在曼彻斯特Christie医院网站,这是一个计划,五年之后,产生了一个活着的生物的卵巢癌细胞。形式的团队现在可以收集samples-mainly ascites-from chemo-naive和复发的卵巢癌患者。他们设法得到超过80体外卵巢癌文化发展。
旅程计划是简单的,这一点不太可能了。“我是在一个巨大的惊喜。我们发现癌症生物学的肮脏的小秘密,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告诉,”泰勒说。“主要癌细胞不会变好文化。"
为什么一个活的生物?
那么,为什么去麻烦吗?卵巢癌是gynecological-related死亡率的主要原因。高档卵巢浆液性癌(HGSOC),最常见的子类型,发展迅速,之前很少被诊断出晚期疾病。治疗选择是有限的和存活率没有大幅提高了20年。
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治疗方法,研究人员需要临床前模型更紧密地反映体内卵巢癌。虽然癌症细胞系是一项重要的资源,他们的局限性。也许最著名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些行之有效的细胞系存在这么久。
“一些发展在文化40、50岁,也许60年。如果你考虑遗传漂变,这些细胞将adapted-do他们真的反映了原始数据来源的肿瘤?”问泰勒。“我们很少了解这些细胞系的起源。没有病理学和他们一起去,肯定没有临床资料。”
模型系统的承诺,更准确地反映卵巢癌细胞的表型和遗传特点,促使泰勒和他的实验室在开发生物生活。如果他们能直接从患者收集和卵巢癌细胞生长,他们可以避免这种遗传漂变和每个文化与临床信息注释。假设上运行的主要障碍是患者样本,他们建立了一个与曼彻斯特Christie和癌症研究中心合作(MCRC)生物并开始收集卵巢癌患者的腹水。
“我们解决了访问问题。我们现在有样品出来我们的耳朵,”泰勒说。“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培养皿中生长,建立细胞系生长像杂草一样,对吧?当我们在主要的巨大惊喜癌细胞不生长在文化”。
绝对的魔法
这个问题似乎是,腹水,而肿瘤细胞的良好来源,也是癌症相关的成纤维细胞生长旺盛,在文化。
“你看到的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和分裂,并最终接管整个盘子,”泰勒说。”,这是毫无意义的。癌细胞是不朽的,而正常成纤维细胞会死为什么他们越来越疯狂和接管我的培养皿而肿瘤细胞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吗?”
分离肿瘤细胞没有表现得更好。他们相信卵巢癌细胞增殖的答案是正确的培养基条件,但知道确切的食谱是症结所在。和它可能仍然所以要不是偶然的评论在CRUK程序授予应用程序审查。
评论家指出泰勒的一篇论文描述了长达10年的寻找的理想培养基人类卵巢癌细胞体外生长。然而,的过程中缓慢。与此同时,路易莎·纳尔逊博士,博士后研究助理在泰勒的实验室,看报纸,决定自己动手。
路易莎说:“为什么我就没有呢?”,我只是觉得,不,没有办法,要细致,配方是如此复杂,”泰勒说。
但尼尔森决心,支付她中工作和泰勒首次实验室可以收集患者样本,然后成功卵巢肿瘤细胞生长。
路易莎·纳尔逊博士,博士后研究助理在泰勒实验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活着的生物的发展。来源:英国癌症研究
“当我们得到了首样生长,这是绝对的魔法,”泰勒说。“往下看显微镜,清楚地看到这些小殖民地的细胞增长。这仅仅是惊人的。”
尽管她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成功的纳尔逊自己的卑微。“我们现在成功率约30%的患者样本的建立作为一种文化,”她说。“这还不理想,但我们正在努力增加通过尝试不同的文化条件和不同的塑料涂层。”
一条通往病人头像
纳尔逊现在运行卵巢癌模型(ocm)生成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生物,有超过80个文化与病例呈上升趋势。这是合作的关键实验室建立了。
“MCRC生物起着巨大的作用,”尼尔森说。MCRC CRUK之间的伙伴关系,曼彻斯特大学和克里斯蒂NHS基金会成立了信任的支持合作研究。
她补充道:“他们配合克里斯蒂临床工作人员让我们收到样品的数量。他们还协调同意后所有患者和为我们提供治疗的细节。没有他们的过程不会是一样的。”
因为活着的生物生成ocm如此相似的特点,卵巢癌,泰勒实验室现在可以使用它不仅探测潜在的生物机制,而且测试新的治疗策略。逗人地,活着的生物概念甚至打开 个性化的方法的可能性卵巢癌treatment-though这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我们能迅速在文化、培养细胞有可能测试的药物或药物组合对每个病人样本,”尼尔森说。“这将是美联储回到诊所,让临床医生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对个体病人药物效果很好。目前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努力。”
这是一个谨慎的兴奋由泰勒共享。“我们想把病人活检和屏幕对药物和经验确定病人可能受益。以这种方式OCM的就像一个病人《阿凡达》。而不用担心描述这些细胞或生物标记…让肿瘤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敏感。”
“但这种方法有很多挑战,”泰勒说。“没有保证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文化,它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我们还没有优化的平台来做到这一点。”
现在,使用生物建立基础生物学的理解已经产生了一个惊喜。中心体的数字分析和高分辨率延时显微显示更明显的异构比建立细胞系中观察到有丝分裂。这一发现导致了一篇论文表明,泰勒说,先进的人类癌症的有丝分裂障碍是低估了。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癌症细胞的显微镜的图像只是看起来不正常,”他说。“你可以告诉马上,有些事情真的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研究这些细胞刚从病人和我们出去很染色体不稳定。然而,细胞存活下来。”
很多泰勒的样本来自病人经历了广泛的化疗肿瘤获得性耐药。“我们离开的时间越长,细胞在文化会变得更加稳定、更加均匀,”他说。”随着他们的发展,一些染色体损伤将丢失。通过研究它们尽快,我想我们克服很多问题我们看到细胞系。"
广度和深度
那么,团队要做的下一个活着的生物?重要的是广度和深度泰勒说。
宽度是simple-he想创建尽可能多的ocm从尽可能多的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任何药物和屏幕上我们所有的样本,”泰勒说。
至于深度,会看到团队专注于单个样本的具体细节。因为流的效率腹水临床样本的实验室,泰勒和尼尔森可以从单一的患者收集纵向样本集。他们可以开始构建一幅肿瘤细胞如何改变的疾病。
“作为一个细胞生物学家我想要的是原发肿瘤细胞化疗之前,我希望复发,治疗治疗疾病看到什么变化,“泰勒解释说。
最后,泰勒是非常敏锐的,活着的生物成为一个合作的平台。
“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有很多的人可以在癌症细胞生物学领域取得进展我们不是专家,”他说。“生物是否成为一个资源为他人,或者我们帮助弥补文化媒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接触并形成合作。”
所提供的英国癌症研究中心